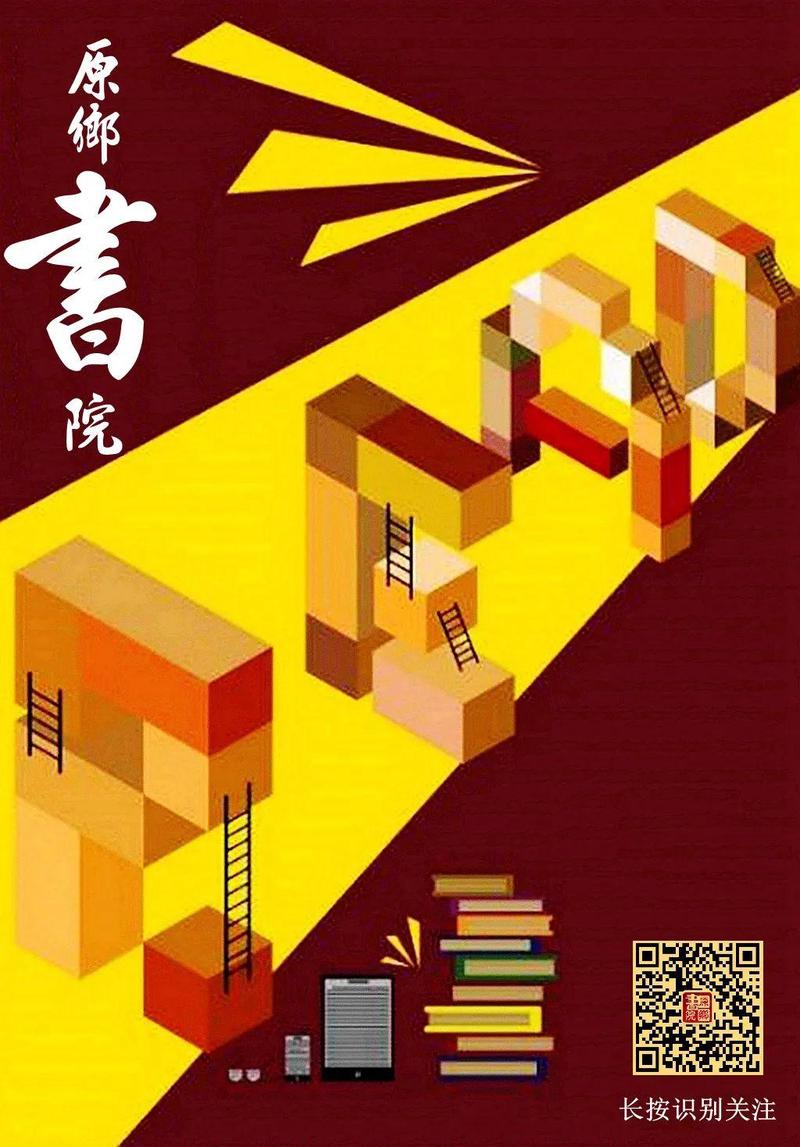博比·安·梅森:高粱饴




丽兹凌晨三点醒来,她听出车道上隆隆作响的车子是丹尼的。那辆车的消音器上有个洞。随后她听见车子调了个头,沿着街道疾驶而去。远处,丹尼在小区街道上来回飙车,轮胎不停地发出尖叫声。她在等撞车的声音,但车子开回来了。丹尼再次倒车,冲上街道,轮胎在尖叫。她吓坏了,心想,会有人给警察打电话。
“爹地在干吗?”卧室过道暗淡灯光下的一个小人影问道。梅丽莎拖着她碎布娃娃的一条胳膊站在那里。
“没事,蜜糖。”丽兹从床上下来,弯腰抱了抱她的孩子。
“也吻一下玛瑞塔·露易丝。”梅丽莎说。
丽兹一只手抱着梅丽莎,用另一只手梳理着小姑娘的头发。为公平起见,她也拍了拍玛瑞塔·露易丝的头发。
“他在开车兜风,宝贝。”丽兹说。“现在路上没车,所有的街道都归他了。”
“爹地不爱玛瑞塔·露易丝。”梅丽莎嘴里嘟嘟囔囔,“他告诉玛瑞塔她长得太难看了。”
“她不难看!她好可爱。”丽兹把梅丽莎弄回到她的床上。“我在这里陪你。”她说,“我们别出声,别把迈克尔吵醒了。”
车子再次轰隆隆地开进车道,车门“嘭”的一声关上了。丹尼在轮胎厂上中班,下午四点到午夜十二点,过去几个周五的晚上,他回来得都很晚,总是醉醺醺的。丽兹在廉价品商店上白班,平日她和丹尼待在一起的时候,两个人都在睡梦里。到了周末,看到醒来并变老了的对方,两人都很震惊。他们就像两地分居的夫妻,她心想,却没有这么做带来的好处。丽兹不再像以前那样爱丹尼了。他喝醉酒的时候,做起爱来就像是在种玉米,她一点儿也不享受。
周四晚饭后,迈克尔和梅丽莎去了住在同一条街上的朋友家玩,丽兹在听收音机里一个有特异功能的女人主持的节目,她叫苏·安·格罗姆斯。
“你好,请讲。”
一个男人说:“能告诉我我会被解雇吗?”
“不会,不会的。”苏·安·格罗姆斯说。
“OK。”那个男人说。
“你好,请讲。”
一个嗓音细长、有点犹豫的女人说:“我把婚戒弄丢了。我该上哪儿去找?”
“我看见一栋高房子,”苏·安说,“带地下室的。”
“你肯定是说我在法院上班的时候。”
“我得到一个很强的画面,一栋带地下室的大房子。”
“好吧,我去那里找找。”
苏·安·格罗姆斯是本地人,中学时和丽兹的哥哥同班。她做这个节目已经快一年了,人们打电话问她金钱和家庭方面的问题,还有很多与癌症和开刀有关的问题。苏·安总有一个答案,就挂在舌尖上,而且她还都能答对。太神奇了。丽兹认识一些给她打过电话的人。
丽兹紧张地拨打电台的电话。她拨了好几次才接通。她需要排队等候,便在厨房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,耳朵里是电话里的音乐声。当苏·安说出“请说话。”时,丽兹跳了起来。她慌慌张张地说:“呃——我丈夫是不是有外遇了?”
苏·安停了下来。心灵感应家通常不会停下来思考。“我的答案恐怕是‘是’。”她说。
“哦。”
接听其他电话时,苏·安·格罗姆斯好像进到了快进模式。生病的孩子、癌症、丈夫失业。答案混成一团。丽兹感到一阵凉意传遍全身。她在商场工作的朋友菲曾劝她出去冒冒险。离了婚的菲周末把孩子扔在她妈家,自己去帕迪尤卡的高级饭店约会。菲不仅追逐男人,她还对有怪癖的人感兴趣。可能是一个养孔雀并自己做苹果酱的老妇人,或者是个跳肚皮舞的。菲曾在“西部酒店”遇到一个跳肚皮舞的,那个女的当初学这门艺术纯粹是为了取悦丈夫,因为她的肚脐能引起他的**,但她却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。她靠跳肚皮舞走遍了全美国,菲说。
天还没黑,丽兹开车出去兜风,她希望自己的雪福来是辆轻巧的跑车。经过“假日酒店”时,她看见旅馆大门上挂着“欢迎德士古石油公司贵宾光临”的横幅。她停在一个德士古加油站加油,琢磨着什么样的贵宾会来这个小镇。因为可以买到烈酒,帕迪尤卡经常举办大型会议。一个脾气乖戾的年轻人帮她加满了油。
“那些贵宾在哪儿?”她问道。
“什么?”
她提起“假日酒店”的横幅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耸耸肩,笨手笨脚地找着零钱。他看上去并不迟钝,只是有点沉闷。丽兹一踩油门冲出加油站。她感到**中烧,但并不针对某个特别的人,她不知道会怎样,但期望迟早会弄明白。在高速公路的一个三岔路口,她放慢了车速,有年轻人在那里擦洗车窗,为白血病募捐。
“为什么我们不偶尔去一次高档点的饭店?”那个周末她问丹尼。菲去过湖边的一家饭店,那里的面包是放在花盆里烤出来的。饭店里装饰着古董和野生动物标本。
“你总想要那些我们买不起的东西。”丹尼边说边拧开啤酒瓶盖子。“你想要一个微波炉,现在到手了。到手的越多,你要的越多。”
她提起他一直想要的奥兹莫比尔牌的汽车(他父亲常用奥兹莫比尔来发誓),不过这么做太费精力了。他一把拽过她来,粗鲁地搂住她。“我怎么你了?”被她推开时他问道。
“没什么。”
“你有点奇怪。”
“我只不过有点沮丧。我想回学校完成学业。我没把大学读完,我应该读完。”
“你上了两年学,可是对你没一点用。这里找不到一份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。”
“我只是希望把开了头的事情做完。”她说。
他咧嘴一笑,用啤酒瓶斜指着她。“厂里一个家伙说他老婆去上学,结果彻底变了个人。她改了发型,还有饭菜的味道等等。他看着她的照片,觉得自己或许被人骗了,她不是原来那个人了。这样的事还真不少。”他若有所思地说。
“总不能得过且过吧。”丽兹怒气冲冲地说。丹尼陌生地看着她。
菲曾对丽兹说起过一个做高粱饴糖浆的人。“我在跳蚤市场认识的,一个讨人喜欢的老头子,他用老式工具做高粱饴。”丽兹特别嘴馋高粱做的糖浆。上次吃这种糖浆时她还是个小姑娘。周五下班后,她开车去了那里。
萨默农场地处五英里外的乡下,靠近一座破落的旧村庄,那里有一家老式的百货商店(油漆剥落,挂着“乐倍”的招牌)。克莱特斯·萨默住在一栋崭新的牧场式砖房里,亮闪闪的白色碟形天线霸气地蹲在后院里。谷仓年久失修,顶已经塌陷,灰蒙蒙的。一个棚子跟前站着几位访客,他们正在围观一个老头在桶里熬糖浆。桶下方的火苗散发出的热浪烤着丽兹的脸庞,她往后退了一步。这个老头已经做了好几十年糖浆,她心想。而她甚至无法让丹尼把鸡烤熟。
那只桶被分割得像一座老鼠迷宫,克莱特斯·萨默用一把铲子让液体在迷宫里流动。他不时铲起浮在表面的泡沫。糖浆是绿色的,像水塘里的淤泥。
“这是第二锅。”他对访客们说。“昨天我花了一整天做了一锅,结果被我倒掉了。味道不对。有股绿味。”
“看上去确实是绿的。”丽兹说。
一个头戴牛仔帽,身穿红色T恤衫的年轻人说:“本来应该让驴子转着圈碾压高粱秆。但是老爸造了一台机器来榨汁。”他笑了起来。“老一辈不是这么做的,是不是呀,老爸?”这个男人皮带的大铜扣上,“ED”两个大大的字母叠在两把交叉的邦联步枪的图案上。“还记得上次那个老农用高粱酿私酒,结果酒被猪喝了,最后还喝醉了?”
男人们大笑起来。老头说:“到处都是吆唤猪的声音!那个老农也被猪撞倒了,昏倒在猪圈里。”他恶狠狠地踢了一脚火堆里的一根木头。“该死的木头!烧不着。它们还完全是绿的呢。”
“这里什么都是绿的。”丽兹说,端详着滑溜溜的糖沫。散落在地上的高粱叶绿油油的。
“过去只要有一家做糖浆,邻居们都会来帮忙。”艾迪说,直直地看着丽兹。她拿定主意他长得很帅。
“现在的人干起活来都不靠谱。”老头咕哝道。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”丽兹问。
“说你干活不靠谱就是说你懒呗。”
后来,在她把买来的一加仑糖浆放进车子里,并停住脚步抚摸猫咪的时候,丽兹又看见了那个叫艾迪的男人,他坐在一棵树下,正在读一本简装书。他体型很棒,有张粗糙坚毅的脸。他朝她笑了笑,一种扭曲的笑容,像贴在糖浆罐子上的标签。
“你住在附近?”她问道。“我从来没见过手里拿本书,懒洋洋地坐在树下的农民。”
“不住在这儿。我刚从孟菲斯赶过来,给我老爸搭把手。我在那里做生意——卖音响。”他合上书,用拇指卡住读到的地方。这是一本关于***的书。
“我一直喜欢往煎饼上抹糖浆,”丽兹说,“但我从来不知道糖浆里面到底有什么。”
“和老爸待在一起是在受教育。他还在用老法子做事情。不过没这个必要了。”艾迪瞟了他父亲一眼,后者正朝糖桶弯下腰,用一把木头勺子品尝糖浆。他似乎还是不满意糖浆的味道。“老爸的状况很糟糕——经常忘事。不过他还是闲不住。他有个女朋友,还自己开车去镇上。顺便告诉你一下,我叫艾迪。”
“我猜到了。我叫丽兹。”
“你最喜欢吃什么,丽兹?”他问道。
“冰激凌,问这个干吗?”
“随便问问。你最喜欢哪个影星?”
“有时候是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,有时候是保罗·纽曼。”
“你想和我一起去吃冰激凌,然后再去看一场保罗·纽曼的电影吗?”
她笑了起来。“假如我丈夫知道了,他会不高兴的。”
艾迪说:“要是‘假如’‘但是’是花生糖果,我们每天都在过圣诞节。”
她大笑起来,他把牛仔帽往下拉了拉,遮住眼睛,从帽檐下方挑逗地看着她。“你丈夫有什么我没有的吗?”他问道。
“我不知道。我从来见不着他。”她说,后悔提到自己有个丈夫。“我俩关系不好。”
“那不就得了。走吧。”
坐上艾迪的红色卡马罗,他们朝帕迪尤卡驶去,走的是小路,经过成熟了的烟草地,盛夏的热浪烤着地里的玉米。艾迪开车很谨慎。丽兹想象不出他会在凌晨三点把邻里搞得惊恐不安。蜿蜒的小路穿过遗弃的小镇和破落的农庄,丽兹觉得很兴奋。原来这么容易。这就是菲每个周末干的事情。
“我死后不想被火化。”经过一个小型家庭墓地时艾迪说。
“现在好多人都火化。我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“我妹妹烧伤了她的狗,兽医不得不让狗安乐死,她把狗火化了,把装骨灰的罐子放在壁炉架上,成了一件古董。”
丽兹感到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她想象自己是一部电影里的某个角色,在女孩遇到男孩的浪漫场景里。她说:“我想看一部新电影,里面有切维·切斯。”
“我以为他已经死了。”
“没死,他还活着。”
“不记得是哪位影星死掉了。”他说。
商场里,他们在一家“睿侠”询问立体声音响部件的价格(“查看一下竞争对手。”艾迪说),然后在商场中央的一个小亭子里换上西部服装拍照。丽兹选了一件低开领的长袍和一条带羽毛的披肩。她在帘子后面换衣服的时候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咯咯地笑着。艾迪选了一顶没有任何装饰的黑帽子、蝴蝶领结、一件绿夹克和带吊带的羊毛裤。开照相亭的妇女说:“你们看上去真棒。拍完这种照片后大家都很开心。我想这会把他们带回到从前那个简单的时光里。”
“要是真有这么个时光就好了。”艾迪点点头,说道。他们在相机前摆姿势时他说:“这是巡回牧师眼中的‘琼斯小姐的诱惑’。”丽兹认出走廊对面鞋店门前一个她认识的女人。丽兹扭过头去,希望没被那个女人认出来,而艾迪则忙着填表格,好把洗好的照片寄到他孟菲斯的家里。
“想吃什么就点什么。”在商场的一家餐馆里艾迪说。丽兹点了卡津香味鸡和一杯玛格丽塔。她从来没吃过卡津香味鸡。价格不菲,不过她觉得艾迪肯定很有钱。她松弛了下来,开始享受生活。她爱喝玛格丽塔。她说:“我店里的朋友菲上周去一个地方吃饭,你从别人端来的一个盘子里挑选肉,然后就在餐桌上自己动手烤着吃。我告诉她说,如果需要自己动手烧,我看不出外出吃饭的意义。”
“你丈夫常带你出去吃饭吗?”
“没有。他上下午四点到半夜的班。而且,他所谓的出去吃就是去麦当劳。”
“他让你感到幸福吗?”艾迪呷着酒,眼睛盯着她看。
“没有。”丽兹说,有点尴尬。“他常喝醉酒,和其他女人鬼混,他才不在乎我干什么呢。”她把通灵家的话告诉了他。
“我曾经让人看过一次手相。”他说,“佛罗里达有个镇子,那里到处都是通灵家。”
“真的吗?”
“真的。我去过那里一次,找了六位看手相的人看我的手相。”
“发现什么没有?”
“我的生命线弯弯曲曲。我会有一个危险且没有结果的人生。他展开手掌,追踪着他的生命线。丽兹看见那根曲线,就像来帕迪尤卡的小路。
“你有孩子吗?”她问道。
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。我结婚的时间从来都不够长。”
丽兹大笑起来。“生个孩子要不了多少时间。”
“你有吗?”
“有——两个,迈克尔和玛丽莎。一个八岁一个六岁。他们把我弄疯了,不过他们是金不换。”
又买了一杯酒后,艾迪说:“有次我看见一个在儿童棒球队打棒球的小孩子。他是个十全十美的小家伙——金头发、蓝眼睛、聪明得像个小人精。他球棒握得很好,跑得也快。你知道我干嘛了?我找到他妈,把她娶了,立刻就有了一个很棒的孩子。一个可以带去钓鱼和玩抛球接球的人。”
“后来他怎样了——还有她?”
“哦,长大后他麻烦不断。不过我在那之前就离开了。”
“说说你自己,”她急切地说,“我什么都想知道。”
丽兹有种满不在乎和自由了的感觉,在那个夏天和秋天,她开始不定期地在周五晚上与艾迪约会。让迈克尔和梅丽莎周五晚去她父母家玩很容易,那里有有线电视。丽兹的借口,和菲以及其他几个姑娘打牌。
(本文为节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