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岭的三月天,乍暖还寒。湿润的空气遇上一场倒春寒,使得城市郊区的小院里处处潮湿冰冷。
外面天还未亮,王甜甜被一泡尿憋醒了,他翻身起来,光着膀子冲进厕所,半分钟后回火速钻回了尚有余温的被窝里。
时间还早,还可以再睡会儿。本来一夜安眠,可临到天亮的这一觉,他做了个梦。
梦里,留善区还叫留善县,他还混在十二刘的拳场里,个子只到十二刘的胸口。十二刘冲他招招手,他小跑着来到十二刘面前。
十二刘兴致很高,要教他怎么以小博大放倒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。十二刘先演示了一遍,壮汉被制服倒地,他看得激动兴奋,十二刘让他上来试试。
他模仿十二刘的动作,抱住壮汉的腿,但壮汉的腿像根扎进地下的柱子,纹丝不动。
十二刘在旁边说:“小子,刚才没好好看吧!”
他不服:“你就是这样教我的。”
蛮力一点用都没有,他满头大汗,壮汉却在头顶笑,像拎鸡崽一样,抱着他的腰把他掀翻在地,粗壮的胳膊抵在他的胸口,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他别过头向十二刘求救:“哥!”
“自己想办法。”
他憋住气,抱住壮汉的胳膊,使出全身的劲儿想冲破压制。猛的一下,他睁开了眼睛。胸口还是有一种被压着的感觉,他掀开身上的被子,喘了口气。
原来是被子,又硬又沉,压得他难受。
这床被子是奶奶手缝的棉花被,他盖了很多很多年,奶奶去世后,被子再也没有拆洗过,虽然有太阳的时候他会拿出去晒,但里面的棉花已经结团了,一点也不蓬松,盖在身上并不舒服。
他起身穿上衣服,坐在床头,拉开窗帘看了一眼窗外,天已经蒙蒙亮了。
拿起床头的手机,拨了通电话,那边很快就接了,是熟悉的、让他着迷的声音。
“甜甜。”
“你起床了?这么早?”
“嗯。刚起。”肖骁捏了捏眉间,坐起来靠在枕头上。
其实他根本没睡。昨晚在熬夜写一个报道稿件,熬了一夜,刚写完,躺下不过一分钟,王甜甜就打来了电话。
“我做了个梦,醒了。无聊,想和你说话。”
“做什么梦啦?噩梦吗?”
“不是,梦到一个对我挺好的大哥,他教我练拳,但是我被一个胖子压住了,压得我难受,然后就醒了。”
“是不是被子太沉了?压住了才做这样的梦。”
“嗯,就是压住了,你怎么知道?”王甜甜很惊讶,肖骁能一下找出重点。
“我也盖过你的宝贝被子啊。换一套吧,那个用的太久已经不保暖了,又沉又硬。”
“这是我奶缝的被子,我小时候就盖这个,扔了怪心疼的。”
肖骁心说,看他有时大手大脚,对奶奶留下的东西倒是深情。
“换床新的,这个先别扔,有太阳的时候拿出来晒晒。 ”
“嗯。嘶~真冷,你今天能来吗?一起睡就不冷了。”
肖骁在电话里笑:“我感冒还没好。”
“来嘛来嘛来嘛,运动一下出点汗就好了,嘿嘿嘿。”
王甜甜在电话里的笑声听起来傻憨憨的,肖骁怼他:“这次感冒就是拜运动所赐好嘛!都是你惹的祸。”
“明明是倒春寒的流感,关我什么事,到底来不来?!”
“晚上过去。”
听到肖骁答应,王甜甜开心地吹了个口哨。
中午,肖骁补觉醒来,出去找饭吃。他一个人很少做饭,太麻烦。只有和甜甜一起时才开火,是两人在一起的乐趣。
常去的那家[阿花盖浇饭]没开门,门上贴了张纸,说店已搬迁至红旗巷。
城市改造如火如荼,留善区的很多老街区老房子上都用红漆画了拆字,面馆所在的这一排老房子也即将拆迁,已经有很多商铺搬走了。
肖骁问旁边五金店的老板:“大哥,红旗巷怎么走?”
大哥给他指了方向,不太远。他打算走路过去吃个盖浇饭。吃饭方面他很专一,在一个地方,认准一家店,一般就不换了。读书时认准了校外符东南的米线店,来到江岭,吃过门口所有的饭馆后,他认准了[阿花盖浇饭]。
这是个常见的夫妻店,阿花是老板娘的名字。老板负责后厨炒菜,老板娘阿花在前面招呼客人。阿花的脸上总是带着笑,看得出来这平平淡淡的日子对她来说是开心幸福的。
他曾经趁客人不多的时候和这对夫妻闲聊,听得一些他们的故事,写成文章发表在文学杂志上,杂志社编辑把读者寄来的信扫描成电子版打包发邮件给他,很多读者说阿花的故事很治愈。
阿花夫妻在自己的世界里勤劳又平淡地生活着,他们不看文学杂志,不会知道他们的平凡与简单居然能成为某些人的心灵良药。
按照五金店大哥所指的路线,他找到了红旗巷。阿花盖浇开张了,桌椅还是以前的桌椅,连墙上的菜单都没换,好几十种盖浇,看的人眼花。
他和老板娘打了声招呼,要了一份木须肉盖饭。店里人多,老板娘在店外的空地上给他撑开了一张桌。
等饭的时候,他看向巷子深处。这个巷子很深很长,周边商铺经营什么的都有,饭馆、杂货店、五金店、服装店、炒货店、熟食店、裁缝店,修鞋店,修表店,配钥匙店……那些在大城市高耸的楼宇间很难找寻到的小店,在这里集齐了。
在层层叠叠的商铺招牌里,他还看到了一家弹棉花店。
弹棉花!他知道弹棉花,小时候听过一首歌叫弹棉花——弹棉花呀弹棉花,半斤棉花弹成八两八。
但他从来没有亲眼见过!
“花姐,饭好了放桌上,我一会儿回来。”
“好~”
他朝弹棉花店走去,一个头发已半白的大娘在经营这家店。他进去的时候,大娘正在一台机器前面处理一堆棉花,机器上棉絮纷飞。
看到来了客人,大娘停下手里的活,用江岭方言问他:“要做新被子还是旧棉花翻新?”
他问:“旧被子能翻新?”
“能,棉花重新弹一下,和新的一样。我们这是电脑弹棉花,弹出来可好了,蓬松又平整。”
“不是人工弹?”
大娘笑:“现在哪还有人工弹的,机器弹的又快又好。”
肖骁心说,是我想多了,都什么年代了,哪儿还能看到人工弹棉花。
他想起王甜甜家里的那床旧被子,既然甜甜那么喜欢,不如给他翻新一下。问了大娘价格,大娘说翻新不划算,你不如买床新的,店里刚进回来一批****,特别好。
他想,还是翻新吧,甜甜对那床旧被子有执念。
出去给甜甜打了通电话:“我看到一家弹棉花店,可以翻新旧被子,一会儿去你家拿被子过来,让大娘重新弹一下。”
王甜甜听说可以翻新,很高兴:“我记得以前奶奶把被子拆掉,变魔术似的,再缝好它就变软和了,原来是弹棉花啊。”
“嗯,看起来挺好玩,不是人工做的,是机器弹的。”
“那就交给你咯。哎?你今天不上班吗?”
“呃…我辞职了。”
“又…又辞职了?”王甜甜的语气相当无奈,他不明白,为什么肖骁换工作这么频繁,感觉这家伙特别随心,好好的工作说不干就立马不干了。
“再找就是了,我工作很好找的。”
“你开心就好。”王甜甜突然大嗓门起来,“有我呢,我卖糖葫芦养你。”
肖骁笑起来:“真哒?”
“虽然我现在也穷,但管你吃穿用度还是没问题的,只要出摊一天就有钱收。你别着急,工作慢慢找,找个好的,稳定的。要是不想找也行,来陪我摆摊嘛,你来写糖人,收入都是你的。”
“呵呵,好呀。”
“要来吗?陪我摆摊。”
“不来,还是要找工作的。”
“哼。”
“会好好找工作的。”
王甜甜那边有生意,他一边问人家要哪一串,一边对电话里说:“先挂了,晚上见。”
回饭馆的路上,肖骁一直在回味王甜甜的话,对面走来的每一个人,都能从他的脸上看到幸福的笑。
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小声嘀咕:“卖糖葫芦养我,嘿嘿,好可爱。”
肖骁不用谁养,他不富有,但给媒体写写稿也足够他生活。前不久,“杨光夏”刚刚把一个城市龙头企业的董事长送进监狱,央视新闻报道了这件事,引用了很多他们的调查素材。
“杨光夏”已经在记者圈名声大振了,他们正踌躇满志地再干一票大的。所有这些,王甜甜都一无所知。
肖骁想过,如果有一天,王甜甜知道了他的真实职业,会怎么样?
他自认为了解甜甜,甜甜喜欢他,就是单纯喜欢,不掺杂任何别的杂念。甜甜是个把信义看的很重的人,有点子江湖气,容不得欺骗和背叛。
所以,如果有一天知道被欺骗了,可能会发很大的火。
但他仍然选择欺骗,他有一堆不得不骗的理由。而且有时候,他有些变态地享受这种谎言下的生活——两个普通的小年轻,在城市一隅,过着平凡的小日子。
回饭馆吃了饭,他去甜甜家找到那床旧被子,拆掉被套,抱去红旗巷的小店里,囫囵交给大娘,委托大娘把被子翻新。
“小伙子,你这个被面还要不要?”
“要哇。”
“那你等我拆了你带走,回去把纯棉布里里外外洗干净,织锦缎不用洗,棉花弹好以后你自己重新缝好。”
“啊?”肖骁不懂。他没睡过这种手工做的棉花被子,不知道要怎么缝。
他看着大娘拆被子,上面一层很好看的布是织锦缎,下面一层有点发黄的纯棉布,拆开后里面的被芯还套着一层棉布,看起来很复杂。
大娘说翻新只是把棉花重新弹软和,做一个被芯。如果要手工缝外面那一层,得价钱。
肖骁眨眨眼,说了句:“我自己缝。”
大娘打量着他:“你?行吗?”
“行。”他说的很肯定。
其实他根本没摸过针线,但很想试试。脑子里冒出来一个念头:“我要亲手给甜甜缝一床软和的被子。”
给大娘交钱,留了电话号码,被芯翻新好后,大娘会给他打电话。
晚上,王甜甜收摊回到家,他已经把被子外面那层纯棉布洗好了,晾在院里。那块好看的织锦缎他叠的整整齐齐收在王甜甜家的储物柜里。
“弹棉花的大娘说,你的被子是以前的人结婚用的,外面那层很光滑的绣花面料是她们那个年代很时兴的好布料。”
“哦,有可能是奶奶的嫁妆吧,奶奶年轻时嫁过两次人,她娘家没人,她自己准备嫁妆,自己缝的。”
王甜甜进屋一坐下,就懒洋洋地往肖骁身上靠,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,随手扔在面前的桌子上。
“什么呀?”肖骁扒开袋子,发现里面装了好几沓冥币。
“马上清明了,回来路上看到卖纸钱的,就顺便买了,过几天拿出去烧了。”
“你买这么多,够烧好几次的。”
“有给奶奶的,还有给大哥和五哥的,大哥今天来梦里找我,肯定是在底下缺钱了。五哥以前最喜欢买名牌,肯定也缺钱。”
“嗯?什么大哥五哥?没听你说过。”
“我有个两个兄弟,前几年出事死了。他们活着的时候对我挺好的,很照顾我。”
“两个兄弟,都死了?”肖骁很惊讶,王甜甜以前没提起过。
“他们在一辆车上,车祸死的。我当时陪奶奶在外地,没见到他们最后一面。害,过去的事,不提了。今天累死了,城管晚上又搞突然袭击,追着我们一帮人跑了一公里,老朱的冷面全洒路上了,我的糖葫芦也没卖出去多少。”
“来,我给你捏捏。”肖骁捧着甜甜的手臂在手里揉捏,“我买了套新被褥,很软很舒服,一会儿去躺下试试。”
听说有新被褥,王甜甜一瞬间弹起来,拉着肖骁的手:“现在就试。”
新被褥很舒服,躺上去打了几个滚就不想起来了,闭着眼睛抱着肖骁嘟囔:“我好困。肖骁,能不能不洗脸,申请睡觉。”
“小脏孩。”肖骁出去弄了条热毛巾,帮他擦了擦脸。
江岭的气候湿润,王甜甜成长在这样的气候里,皮肤细腻,滑溜溜的,很好摸。他摸了两下,又凑上去亲了一口,戳着甜甜的脸蛋:“骗子,谁说晚上要运动一下的。”
还没睡实的王甜甜憨憨地笑:“等我睡醒,我太累了,快来嘛,抱着暖和。”
几天后,肖骁从大娘店里拿回了翻新的被芯,又软又蓬松,比之前的被芯厚了一大截。他甚至怀疑大娘是不是拿错了,给他拿了新棉花的。大娘笑说:“就是你家的被子,没弄错。真棉花被就是这样,永远不会坏,多拿出来晒晒太阳杀菌,用一辈子都没问题。”
为了缝好被子,他特意请教了大娘,在大娘那儿买了针和线。大娘倒是不吝啬,认真给他讲了一遍。临走时看到大娘店里有一些带花梗的干棉花,他问那些花怎么卖,大娘说你喜欢就拿几朵,不要钱,他要了好几朵。
回到家就开始缝被子,没拿过针的大小伙子,缝的磕磕绊绊,手上被扎了好多针眼。
他抬手看看手上的针眼,自嘲道:“和我的心眼子一样多。”
缝被子目的不纯,一方面确实是想为甜甜做点事,另一方面,他心里打着小算盘。他想,以后要是甜甜知道了我对他的撒谎,他想起我的好,也许会更容易原谅我。
二十几岁的肖骁,满腔热血想做一番伟大的事业,做一个能影响社会、利国利民的优秀记者。他可以为了爱情留在一个城市,他也可以为了他的事业果断抛弃他的爱情。
一开始就选择撒谎,因为他那时候觉得,爱情是可以随时抛弃的。在他心里,王甜甜不是最重要的。
可是,最是人心难以捉摸啊。在一起的日子越久,他的心里逐渐生出了恐惧和担忧,对未来的担忧。他担忧谎言被戳破,担忧因谎言而失去他的甜甜。
他开始深谋远虑地给未来铺路,用八百个心眼子给王甜甜下温柔陷阱,让王甜甜记得他的好。
王甜甜收到了翻新的被子,看到了他满手的针眼,骂了他一顿:“你是不是傻,你不会缝你就别缝,你看看把你扎的。”
他嬉皮笑脸:“能省则省嘛,让别人缝还要手工费呢,我已经学会了,以后家里的被子拆洗就交给我咯。快摸摸,是不是软和多了。”
王甜甜白了他一眼,瞥见家里多了个“花瓶”,用透明酒瓶做的,上面扎了几圈不知哪里捡来的细麻绳,瓶子里插了几枝毛绒绒的花。走近一看,是干棉花。花瓶旁边还放了一张纸条,纸条上写了一句话:我想和你做两朵棉花,互相温暖,永不变质。
肖骁问:“好看吗?大娘给我的。”
“挺好看的。”
“大娘说真棉花永远都不会坏,可以放一辈子,我要了几支回来。”
“你可真会捡便宜。”
肖骁眯眼笑:“是不是很会过日子?”
王甜甜点头:“嗯,比我会。”
他拾起桌上的纸条,拿回房间,夹在他的记账本里,抿起嘴偷偷笑。
肖骁从来不说肉麻的“我爱你”,但别样的表达也能搅动他心里的一汪春水,比如今天这句:我想和你做两朵棉花。
一辈子都不会坏的棉花,互相温暖的棉花,也是他们永不变质的爱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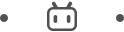
日子过的好快呀,又到周末啦,周末愉快~
